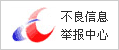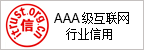发财图 1927年 齐白石
诚然,书画家笔下所有的“添补”未必都是“救场”,但有些别具用心苦心的惨淡经营确实都有“救场”的功效。最典型的画例,可举《世说新语·巧艺》记“(晋)顾长康(顾恺之)画裴叔则(裴楷),颊上益三毛”。益,添补。三,虚数。三毛,非实数“三根须毛”(有人译作“三根须毛”,不符古汉语本意)。“颊上益三毛”,即在颊上添画了数根须毛。当时“人问其故”,请教过顾恺之,顾认为俊士裴楷“儁朗有识具”,仅画出容仪外表形似,不算成功;非颊上添须,显不出裴楷特有的聪慧才具。添须完毕,果然灵气俱现,“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超胜)未安时”(添上几笔,比没添须毛时,顿时神似精彩殊胜)。这“颊益三毛”就是“盘活画面”的“一步好走”。有之则“能盘活成好画”,无之则“僵局死棋,那画就要不得了”。
类同的画例很多,如果还检顾恺之艺事说话,例如顾恺之画人传神,迟迟不肯点睛,一点即活灵活现,曾曰“点睛之节,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见《历代名画记·画赞》),又曾为眇目的殷仲堪画像,想了个“救场”的好主意,顾先“明点眸子”,然后“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也就是说,用“飞白”(书法笔法)如“轻云之蔽月”,淡淡遮过先画好的“明眸”,遂遮掩了殷仲堪的眇目残疾。如此,救得缺陷等于救画。
以上三例虽然在《世说新语》中都捎带着魏晋述事文风的神秘感,但画理昭昭其然。读者若当画家轶事过眼一笑,是一种读法;若当“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失之则伤局”(林纾《春觉斋论画》),知笔下即兴的“那一步好走”是“盘活好画”的“救场”,又是一种读法。神气,可通神韵神似,难怪东坡要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个中理趣,唯识者知之。
当年潘天寿先生评议顾恺之画艺画理有五则著名论述,其中谈到顾的“迁想妙得”“颊益三毛”时,认为“凡事有常必有变:常,承也;变,革也。承易而革难。然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非一朝一夕偶然得之,故历代出人头地之画家,每寥若晨星耳”(《听天阁画谈随笔》),画理至明。因为“凡事有常必有变”,画事也非例外,所以,顾恺之的非常之革,有常之变,也绝非只拘拘于“颊益三毛”,曰补曰救,称名而已,唯激活创造性思维,开阔眼界,足资深味。
这种“盘活画面”的“添补”,即兴性很强,没有预设的框框,故而每经画家笔下一救,或可形神合一,遂臻妙境。笔者曾建议国家画院学子,观赏近代吴昌硕、任伯年画的牡丹和水仙图,不妨同时关注画中那些直正欹斜的片石或其他物件,读出其用心,再细细体味宋董逌《广川画跋》所言“石亦活物”等画论,方有真悟。据郑逸梅《艺林散叶》曰,缶老自谓“好画绝无闲笔”,“画牡丹易俗,画水仙易琐碎,只有加上石头,才能免去这两种弊病”。如果花是主,其叶其石皆为客,是主客相形,主客陪对,还是反客为主,喧宾夺主,一般预有主意格局,意在笔先,皆非凑泊;苟有变化,迁想妙得,随法生机,下笔即时可救。所以,面对经典,读画者岂能过眼了得?只看牡丹水仙,设色浓重明快,布置密实空疏,是一种读法。再看配图的突兀单石或者高矮错落的组石在图中扶花间叶的相势变化,其虚实出入,相扶相救,俨似天成,如何最终示出整幅的精彩,也是一种读法。看来,出浅入深,能否窥取其意气所注,都在自己。
或谓缶老花石浑然,纵有先后主次分合,未必是失是救。其实,是失是救,缶老的夫子自道已经讲得相当明白,免去弊病无异“救场”。不过就读画者而言,重要的是观看经营位置(空间组合),读懂其先后主次分合搭配的微妙,活眼通灵的目的总在窥取门道,未必都要去读画家“自供”。
齐白石作于1927年的《柴耙图》,耙竿一线直下,下缚柴耙七齿,画幅左侧先题七律附跋并添注(共五行,113字),整体观之,不仅单调平齐,画幅也明显右倾左重;齐白石遂于右侧添加33字跋语说明画《柴耙图》的原因,予以补救(既补文意,又补构图)。右跋一行贯下,与耙竿平行,几达画底,如此两跋对举,耙竿一线居中,突兀醒目,翻收意外之妙。
面对此画,读画者说左右两跋原本如此也好,说右跋后加或者左跋后添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读画,只要两跋并观,刻石图龙,只赚不赔,便是好画。倘若遮去一跋观之,立即窥出画面欹倾的缺失,自去理会个中“救场”的作用,便是长进。
可以同样的眼光,再去读齐白石的《发财图》。此图下半偏右画一算盘,上半行书题述来客求画《发财图》并与之对话的大段文字(十行128字),书侵画位,大有压顶之感。齐翁遂以“三百石印富(脱漏‘翁’字) 制于燕”,补救右下,似为支撑,如此构图方得安然。上半大段必是先题,末尾纵有“三百石印富翁又题原记”,是因为“客去后,余再画此幅,藏之箧底”,故而“又题原记”(指按前画的题记文字又照录一遍)。与《柴耙图》一样,遮去大小任一题写,构图偏侧,其病即见。见者能知得失,即是一得。
非独构图如此,绘画中以设色救场也不少见。为方便说法,可举齐白石的《荔枝图》为例。此图荔枝颗颗鲜红,中有两颗黑色荔枝。观者初看,以为唐突;再观,觉得黑果衬托红果反而更加鲜亮真实。汪曾祺先生说,观看展览时正好李可染先生在场,可老说他曾有幸亲见白石老人画的这面册页,最有发言权。当时作品已近完成,老人端详后忽然拈笔濡墨,飞出了两个黑荔枝,全画遂生机活泼。妙得意外,如同清风自来,偶然在必然之中。因“特殊十年”中有人曾拿黑荔枝批判过“齐木匠黑红不分”,故笔者二十年前主编《当代书坛名家精品与技法》时,汪先生著《论精品意识》一文,定要将齐白石画“黑荔枝”事写入,以为“黑果救得精彩”。惜此书拖延至戊寅(1998年)夏出版时,汪先生已经故世,笔者乃以此文为序,亦是铭记老前辈点拨教诲的苦心。
书画家笔下忽有缺憾,能缺失后善救,亦称高手。读画者呢,看得假魏王的“雅望非常”,已不简单;窥出“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愈是明眼。学习,非为重复缺憾,只为直取精髓,“须参活解”(清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能“悟其所短,恃其所长”,“益进于通方之妙”(明项穆《书法雅言》),方为善学。(作者为诗人、学者)
责编:文化中国网 张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