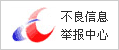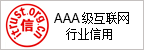海清去年一整年都在拍戏,忙得有点“错乱”,所以今年缓下来,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开工,也是想借机会,把眼前的事情一桩一桩捋捋清楚。她知道自己是快不起来的人,也不需要那么多人爱她,自己爱自己,就足够了。
她也在这些年里渐渐想明白很多事。无论演戏、看戏,都是自我和角色之间的事。“你喜欢那个角色,其实喜欢的是你自己;你若不喜欢,那让你不想直视的,其实也是你自己。这些都是观众和角色之间的事,和演员无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几乎很少和观众作直接的交流,很少接受采访,讲自己的事,她还是愿意通过角色和观众交流。“我的角色是我的角色,你看到的那个角色,是你生活中的角色,我们会有一些重合,但我们没有办法做交换和替代……你喜欢,我会演;你不喜欢,我还是会演。”
海清窝在茶室的藤椅里,幽静的音乐在耳边似有似无。见面的前几天她因为几地奔波生了重感冒,嗓子发炎到几乎说不出话来。来赴约时也没好透,穿着一身棉麻质地的格子长衣长裤,闲适得像在自家客厅。房间很大,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她说话的声音依旧轻曼,含着,有南方女人的温润,亦不乏坚韧。
讲起儿子蛋妞海清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之间太多美好动人的事情,她说要找个机会好好记下来。而说起表演和生活,眼帘却不自觉低垂下来,沉静入心。这些年他接受了一件事,每个演员的外在、说话的声音、眼神、对一样事物的反应,就像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角色,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演法,只属于个人,学不来。所以现在她相信,与其从外部改变和学习表演的技巧,不如从内在去锻造自己。“你的心态改变了,外部自己会有变化。这是两条路。”她并不是要刻意去突破什么,只是想在“往外走”和“往里走”里,选择后者。
“每个角色像一个笼子,你在里边。有的笼子你很好控制,稍微一伸展。笼子就会按照你的形状变化,那就是非常容易上手的角色。有的则完全不一样,你进到笼子以后发现,笼子不合适,让你要很痛苦地去扭曲自己。”相比于这个比喻,海清更希望达到的是与一个角色完成“气息”上的交换与互融,“它不是笼子,而是一股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头,就是长在你心里的。”
过去她向往一种创作的境界是自由,后来了解到,有一种比自由更高的境界叫逍遥,很吸引她。“我在戏里面尽量做到自由,但我知道我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这些能够瞒的过观众,瞒不过我自己,更别说逍遥……”
逍遥曾经有过,是在她小时候跳舞的时候。“每次跳舞去拿奖的舞蹈我都从来不编排,我哪知道我要跳什么,我听见音乐一响,想跳什么就跳什么了。”七岁的时候,六一儿童节全校比赛演出,她当时就是这么跳的,拿了奖,老师说这孩子真好,给她配了四个伴舞,要排演《阿里山的姑娘》,海清和老师说,你不要给我排,你排她们的,不要排我的。“我小的时候跳舞是逍遥的,后来长大学了好多东西,规范动作什么的,那个境界就再也达不到了。”
现在她最享受的,是蛋妞在家里玩儿,一块“演”。“我们俩演两只狗,流浪的狗,还不能说话,就得让看的人知道我们俩很饿……还演沙漠,一阵风吹来,我就把屁股撅起来,跟蛋妞说,你看沙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一阵风吹来,沙子散了,我就在床上滚,他可爱跟我玩这个游戏了,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他有时候会特别坏,突然一下他自己冲起来,坐到我屁股上,沙子平了。”夏天,洗过澡,不开空调,两个人就趴在床上,可以一玩玩很久。
海清知道,自己期盼的那种天然的逍遥,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她现在时而会想起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迷茫,天天去教室里看电影,看到《8又1/2》里面那个男主角特别不开心,想去寻求人生的答案,他找到一个神父,问他,为什么我觉得我的人生这么痛苦,为什么我不快乐?教皇说,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这一句话,让海清思索好久,“我害怕这句话是对的,但我又预感这句话可能是对的。”然后她就去找“师父”黄磊,也问他,为什么人生是痛苦的?“他说,对啊,所以人在不停的寻找快乐。”
那一年,海清二十一岁,突然知道了生活的真相,后来她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想证明这个真相是错的,“然后今天你发现你无法证明这个是错的,你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是对的……越来越清楚人生是由太多的苦组成的,所以会更加珍惜。”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海清突然问爸爸,人为什么要死?人死了以后去哪?那我的心到哪去了?我会变成鸟吗?还是我会变成泡泡?我爸一个都答不上来,说,要死也我比你先死。
儿子蛋妞在三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在外面玩,玩完回家,一路上脑袋蔫蔫地搭在海清肩头上,她问蛋妞,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不高兴了?蛋妞小声自言自语说:“我活着有什么意……”海清一直回忆,却越发不慎确凿,到底儿子当时说的是“活着有什么意思”还是“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就觉得太奇妙了,一个三岁的小孩怎么会说出来这样的话来。我说妈妈也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在哪,妈妈也在找,我说如果妈妈先找到,妈妈告诉你;如果你先找到,你告诉妈妈。”
责编:文化中国网 刘铭